唐帝國安史之亂本不該持續(xù)八年 都是內(nèi)亂惹的禍
大唐天寶十四年(755年)十一月,范陽、平盧、河?xùn)|三鎮(zhèn)胡人節(jié)度使安祿山,在北方陰險的蟄伏了多年之后,終于向唐帝國亮出了可怕的猙獰面目。十五萬叛軍,攻城掠地,荼毒中原大地。對盛極一時的大唐帝國來說,這哪僅是晴空霹靂;簡直可以說是頂級大地震了!
安祿山起兵反叛大唐,打出的是“清君側(cè),誅殺楊國忠”的旗號;明顯有欺世盜名的成分。不過安祿山想干掉楊國忠也并不是假的;從他自己來說,他要是再不趁著有兵權(quán)之時反叛,宰相楊國忠遲早也要鐵了心找茬把安祿山給做掉。安祿山,楊國忠,從最開始的互相不對付,發(fā)展到后來已經(jīng)是勢同水火。楊國忠早就公開對唐玄宗說,安祿山要謀反(可惜李隆基就是聽不進(jìn)去)。一國的宰相天天在皇帝耳邊吹風(fēng),安祿山自己心里也確實有鬼,不可能不哆嗦;到后來干脆發(fā)展到楊國忠令人“刺求反狀,諷京兆尹圍其第,捕祿山所善之李超、安岱、李方來、王岷殺之,貶其黨吉溫與合浦”。與安祿山關(guān)系鐵的人,已經(jīng)有被殺掉的了。所以他再不反叛,腦袋必將保不住(劉宋殺檀道濟(jì),趙宋殺岳飛,人家明明沒有反狀尚且以“莫須有”就誣陷誅殺;何況安胡兒是真有反心?)
從大的方面看,安祿山能夠重兵反叛,也是拜唐朝邊鎮(zhèn)權(quán)力過于集中、中央與地方權(quán)力失衡的原因所賜。安祿山反叛之前,唐玄宗自恃國力強(qiáng)盛,銳意開發(fā)邊疆,猛將勁卒多聚于外;而與此同時,唐帝國原有的府兵制已經(jīng)衰落(明朝的軍戶制、軍事衛(wèi)所制度跟府兵制是異曲同工);關(guān)中、京師地區(qū)原本兵力雄厚,此時卻早已空虛;相比募兵制的邊鎮(zhèn)軍事力量,數(shù)量、質(zhì)量上明顯是“內(nèi)輕外重”之格局。而安祿山,更是由于玄宗愚蠢的寵信,得以身兼范陽、平盧、河?xùn)|三鎮(zhèn)節(jié)度使;權(quán)力之大,完全有同中央政府叫板的本錢。唐帝國全國也不過設(shè)了十大節(jié)度使啊!
從軍隊質(zhì)量和戰(zhàn)斗力來看,安祿山的叛軍,在起兵前,就經(jīng)常與契丹、奚這些草原騎兵打仗;作戰(zhàn)經(jīng)驗可謂豐富;到后來東突厥阿布思部加入后,可稱得上是精銳猛將云集了。反之,唐帝國因為承平日久,內(nèi)地久不經(jīng)戰(zhàn)事,所以戰(zhàn)爭初期,叛軍勢如破竹,攻陷黃河以北大片土地和城池。唐玄宗的腦袋這回終于被安祿山的大棒子給砸醒了。李隆基,當(dāng)初那么多人告發(fā)安祿山有反意,他卻將告發(fā)者治罪或逮捕;有的干脆綁著送給安祿山叫他殺。豺狼,都是自己一手養(yǎng)壯的!
后悔是沒用啦。唐帝國開始在全國動員抵抗叛軍的軍事力量。安西節(jié)度使封長清,是高仙芝一手提拔起來的西域邊陲大將。唐玄宗召他入朝,決定讓他來統(tǒng)兵抵抗叛軍;并詢問其平叛作戰(zhàn)方略。封長清對唐廷忠心耿耿,且久席邊事,慷慨回答:“安祿山率兇徒十萬進(jìn)犯中原,太平日久,人不知戰(zhàn)。但勢有逆順,勢有奇變,臣請走馬赴東京,開府庫,募驍勇,計日取逆胡之首懸于闕下!”(《大明劫》片中,孫傳庭起初豪壯的說過“破賊,五千精兵足矣”,兩個人倒挺像,呵呵)
李隆基“聞言壯之”。也難怪,多長時間了,官軍節(jié)節(jié)失敗,叛軍鋒芒如日中天,這個節(jié)骨眼,聽到這些是太提氣了。玄宗遂任命封長清為范陽節(jié)度使,命他前往洛陽募兵,抵抗叛軍。
封長清到了洛陽,隨著接觸實際情況,就發(fā)現(xiàn)自己錯了。心情也沉重了。因為他久居西域邊陲,并不了解內(nèi)地的實際情況。實際情況是他自己大吃一驚。內(nèi)地的軍隊,由于承平日久,長期不打仗,戰(zhàn)斗力與久經(jīng)戰(zhàn)事的邊陲軍隊相比,簡直是“不堪用”!此前只是知道“太平日久,人不知戰(zhàn)”,沒想到“人不知戰(zhàn)”的程度,豈止是單單沒有作戰(zhàn)經(jīng)驗的問題,已經(jīng)達(dá)到了“不堪一用”。內(nèi)地的軍隊,怎么萎靡成這樣了?——這個,倒是不能怪封長清在皇帝面前“吹牛”。封大將軍還真不是愛吹牛的人。他是高仙芝一手提拔的安西都護(hù)名將,文武雙全,久經(jīng)戰(zhàn)陣;在安西統(tǒng)帥的軍隊,也不是渣。只是實在是沒想到,內(nèi)地的兵將,戰(zhàn)斗力都頹廢成這樣了。不經(jīng)過調(diào)查研究,就沒有發(fā)言權(quán)啊!可是現(xiàn)在說別的,又有何用呢?
封長清心痛之余,卻并未退縮,仍然積極募兵。“旬日得兵六萬,皆傭保市井之流”——募來的兵,有大量老弱殘兵;有的連箭都不會射,有的連馬都騎不了,上街維持維持秩序,管管“市井”還行。這哪趕得上安西的那支久經(jīng)沙場的精兵!明知不可為而為之,封長清依然以一個職業(yè)軍人的敬業(yè)精神,組織這支新兵部隊開始訓(xùn)練。
可是光有敬業(yè)精神不行,關(guān)鍵是此時已經(jīng)來不及了!天寶十四年十二月,叛軍渡黃河,攻陷陳留!之后馬不停蹄,兵鋒直抵葵園!此時封長清募集來的軍隊,才訓(xùn)練了沒幾天。一支新兵部隊,要想練到有哪怕有基本作戰(zhàn)能力的程度,短短幾天簡直是九牛一毛。
這樣危急的形勢下,封長清表現(xiàn)出了一位職業(yè)將領(lǐng)的堅強(qiáng)勇敢,他面對兵鋒正銳的叛軍,毫不退縮,親率一支戰(zhàn)斗力相對強(qiáng)的驍騎與叛軍前鋒接戰(zhàn),并英勇的發(fā)動反沖鋒,殺敵百人。叛軍主力蜂擁而至,封長清見自己兵少,退守東門。此時,募集的新軍戰(zhàn)斗力低下的問題就一下暴露出來了。叛軍以鐵騎沖突,封長清的新軍連門都沒守住,潰不成軍。然封長清不愧是大唐鐵血軍人,繼續(xù)率軍在都亭驛與敵血戰(zhàn);再次不敵。連番血戰(zhàn)后,封長清已是寡不敵眾,無奈退往陜郡。此時,高仙芝率領(lǐng)五萬軍隊,正在陜郡駐守。遺憾的是,此時高仙芝手下的這五萬兵馬,跟封長清在洛陽招募的軍隊一樣,是剛從長安招募的新兵,戰(zhàn)斗力同樣低下;跟當(dāng)年遠(yuǎn)征阿富汗,在恒邏斯戰(zhàn)役與阿拉伯大軍血戰(zhàn)的那支部隊沒法比。那場大戰(zhàn),雖說是唐軍大敗;但那支唐軍部隊畢竟稱得上是精兵。
所以,身經(jīng)百戰(zhàn)的高仙芝也冷靜的認(rèn)識到,靠這樣的軍隊去打仗,是送羊白白入虎口,這樣的無謂犧牲必須避免。兩員帝國大將最終決定,堅壁清野,向潼關(guān)戰(zhàn)略撤退。撤退途中,部隊遭受叛軍截?fù)簦瑩p失人馬甚眾;但高仙芝、封長清終于成功將部隊主力撤到了潼關(guān)。潼關(guān),與黃河渡口和崤山天險結(jié)合,號稱天下第一雄關(guān)、天險,地勢險要;早在春秋戰(zhàn)國時代,就是關(guān)中秦地的門戶。叛軍圍殲高仙芝主力,進(jìn)而閃擊潼關(guān)的企圖落空,叛軍大將崔乾佑只能望關(guān)興嘆。兩員帝國大將這一正確的戰(zhàn)略撤退,不僅避免了無謂的犧牲,更為大唐贏得了關(guān)鍵的喘息機(jī)會。這個可不能小瞧;從這一刻起,對大唐軍事態(tài)勢有利的局面其實已經(jīng)無形中邁出了第一步。
為何說這是有意義的第一步?往下說就明白了。因為之后,唐帝國的平叛戰(zhàn)爭,贏來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(jī),或者說是唐帝國能最終打敗安祿山的一個至關(guān)重要的拐點(diǎn)!這個機(jī)會如果把握好了(其實唐朝政府軍也曾經(jīng)一度抓住了這個良機(jī)),我看安史之亂就不會禍亂大唐長達(dá)八年了;有可能兩三年就結(jié)束。而如果短短幾年就平叛成功,大唐帝國后來也不可能出現(xiàn)那么多的蝴蝶效應(yīng)!
言歸正傳。此時的態(tài)勢,是叛軍南線閃擊潼關(guān),直搗關(guān)中的企圖化為泡影。但北線,安祿山也沒閑著。他派出大將高秀巖,率鐵騎進(jìn)攻關(guān)中北部的朔方。朔方一旦得手,北線的叛軍就可以南渡黃河,從草原向南,威脅長安;這也正是歷代草原民族進(jìn)取中原的路線。想的計劃倒是挺好,然而北線叛軍這回卻到底碰上了一個狠茬;這個狠茬就是唐帝國名將,朔方節(jié)度使郭子儀。郭子儀統(tǒng)帥的部隊,與高仙芝封長清招來的新兵不一樣,是久習(xí)邊事的大唐邊鎮(zhèn)部隊。所以高秀巖叛軍和郭子儀的軍隊一交手,終于知道了什么叫不慣病,高秀巖叛軍一戰(zhàn)就被打得潰不成軍。郭子儀這還沒完,果斷乘勝咬著叛軍又一頓狂扁,攻克山西的靜邊軍城。這個地方被唐軍占領(lǐng),叛軍太難受了;叛將薛忠義統(tǒng)兵瘋狂反攻,結(jié)果又被郭子儀一頓暴揍,七千胡騎被唐軍殲滅。不可一世的安祿山叛軍,這次終于領(lǐng)教了唐帝國軍隊的厲害!
之后,郭子儀大軍馬不停蹄,根本不容北線叛軍喘息,接連攻克云中(大同)、馬邑、雁門關(guān)。此時的戰(zhàn)略態(tài)勢,已經(jīng)對唐帝國變得有利了。唐軍在北線的反攻,導(dǎo)致安祿山起家的老根據(jù)地一帶幾個戰(zhàn)略要地喪失。唐軍南可南下河?xùn)|;東可出兵河北;安祿山再不能像以往那樣,毫無后顧之憂的南侵;唐軍在叛軍背后,安祿山猶如芒刺在背,這哪里是刺啊,簡直就是釘進(jìn)安祿山后背的大釘子。安祿山是接招也得接招,不接招也得接招。南線的叛軍,必須被迫分兵往回抽。這顆可怕的大釘子要是再不管,北線唐軍會繼續(xù)行動,直至將叛軍的南線北線斷開;斷開了南北兩線就各自都成了孤棋,那這個棋局可真就馬上要翻盤!
這個最關(guān)鍵的節(jié)骨眼,唐帝國自己內(nèi)部竟然出事了。一步臭棋,臭不可聞,幫了安祿山的大忙。起初高仙芝封長清出兵,由榮王(皇子)李琬為元帥,宦官邊令誠為監(jiān)軍。李皇子到任不長時間,竟暴病身亡。他這一死,邊令誠就更得瑟上了。明明用兵打仗他是外行,可他仗著是監(jiān)軍,經(jīng)常亂干涉軍務(wù)。這還不算,邊令誠還總求高仙芝辦事,高仙芝都沒答應(yīng)。你平時也就算了,現(xiàn)在這個戰(zhàn)局,你一個軍事外行過來瞎攪合,那不是讓軍隊遭殃嗎?再說潛規(guī)則那一套,以前就沒少送你財物,現(xiàn)在這么嚴(yán)峻的情況你還沒完沒了,我高仙芝又不是提款機(jī),哪能沒完沒了的答應(yīng)你,將士們和戰(zhàn)馬都要吃飯,都要用錢,現(xiàn)在發(fā)放給將士們的物資都不足,你讓我上他們手里搶?所以邊令誠的欲望,并未得到滿足。這個小人心如毒蝎,回朝惡毒的向玄宗奏了一本:封長清在皇上面前說大話吹牛,而到了前線又畏敵如虎,總是夸大叛賊的實力而動搖軍心;高仙芝又無故拋棄了陜郡幾百里國土,還偷盜、克扣朝廷下發(fā)的軍糧與賞賜。而東都洛陽卻被叛賊荼毒。這兩個人是欺上瞞下。此外,邊令誠又詳盡的報告了高仙芝、封長清戰(zhàn)敗的情況(免不了添油加醋),而對二將的頑強(qiáng)血戰(zhàn)、二將帶兵的辛勞、新兵戰(zhàn)斗力低下等問題,故意隱瞞不報。李隆基聽后大怒,做出了愚蠢的決定:把這兩個混蛋給我殺了!這是腦袋叫門給擠了之后下的旨意。這股“果斷”勁,早用到安祿山頭上,哪會有今天呢?這么亂殺胡殺,唐玄宗也不想想,以后誰愿意給你打仗!或者就算為你打仗,誰又不多留個心眼?(這點(diǎn)跟明朝崇禎有一比)
高仙芝,封長清,兩員帝國優(yōu)秀將領(lǐng),就這樣冤死于邊令誠奸佞之手、李隆基之愚蠢。封長清臨死前悲壯的留下了《封長清謝死表聞》,內(nèi)容慷慨激昂且悲壯,“仰天飲鴆,向日封章,即位尸諫之臣,死做圣朝之鬼。若使殆而有知,必結(jié)草軍前。回風(fēng)陣上,引王師之旗鼓,平寇賊之戈。”封長清慷慨赴刑后,高仙芝也巡營回來,剛聞聽封長清被斬首,又驚又怒。邊令誠懼怕高仙芝反抗,急招陌刀手百人跟隨,說:“大夫亦有詔命。”高仙芝立刻明白,自己同樣是難逃一劫了。之后邊令誠宣讀敕書。高仙芝聽罷說:“我遇敵不能戰(zhàn)而退兵,的確有罪;今上頂天,下踩地,道我克扣士兵錢糧與賞賜,乃冤枉我也!”此時已經(jīng)聚集了大批唐軍將士來圍觀。高仙芝扭頭大聲說:“我于京師招募爾等出來作戰(zhàn),諸位雖得到一些兵餉物資,然遠(yuǎn)遠(yuǎn)不足。正欲與諸位兒郎一道沖殺破賊,取高官厚賞;不料賊眾突來,方撤兵至此,本已乃為國家固守潼關(guān)。若我果真克扣了你們的錢糧,你們就說有;若我未曾克扣錢糧,請你們說無!”士兵們齊聲大喊:“無!”并大呼高仙芝冤枉,聲震天地。邊令誠恐事情有變,急命行刑。
兩位將軍就這么窩窩囊囊死了。
兩員能打仗的大將,唐廷自己幫助安祿山給除掉了。其他節(jié)度使,要么遠(yuǎn)在南方,要么無法及時來到關(guān)中,朝中武將,一時無人可用。唐廷緊急起用在家養(yǎng)病的哥舒翰,命其討伐安祿山。哥舒翰稱病推辭,玄宗不準(zhǔn)。唐玄宗還號令全國四面出擊,收復(fù)洛陽。于是哥舒翰率高仙芝舊部和其他各路軍隊,號稱20萬,鎮(zhèn)守潼關(guān)。此際,北線叛軍高秀巖,進(jìn)攻郭子儀,又被擊敗。
哥舒翰也是久經(jīng)沙場的老將,同樣堅持高仙芝封長清那一套,就是不出關(guān)去野戰(zhàn),叛軍遷延日久,活活被拖在潼關(guān)之下,想打哥舒翰又不跟他打,白白消耗糧草與軍事物資。
756年,天寶十五年5月,唐朝名將郭子儀(朔方節(jié)度使)、李光弼(河?xùn)|節(jié)度使)在河北嘉山,聯(lián)手大破史思明叛軍。史思明部隊被殲4萬余人,一千余人被俘;史思明本人落馬,靴子也掉了,光著腳丫子拼命逃走,夜間拄著一桿半截槍桿狼狽不堪的回到軍營;之后又逃往博陵;李光弼又率軍圍攻博陵。唐軍聲威大振。河北十余郡紛紛殺死叛軍的守將,向唐軍投降。忠于唐室的大批地方官,也紛紛策反。這可是安祿山的老巢啊。淪陷地區(qū)的百姓,苦于安祿山暴政久矣,也相繼起來反抗。洛陽至范陽的道路也被唐軍切斷;叛軍往來都是輕騎悄悄經(jīng)過,還經(jīng)常被截殺俘虜。這樣的軍事態(tài)勢和戰(zhàn)略局面,對唐帝國來說,是形勢大好。安祿山叛軍不得民心,照此發(fā)展下去真可謂會陷入了人民戰(zhàn)爭的汪洋大海,而人民戰(zhàn)爭在孫子兵法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看來,是敵人最怕的戰(zhàn)爭。唐廷如果照這個局面正確的一步一步走下去,安史之亂的歷史可就真要改寫了,那這場平叛戰(zhàn)爭的進(jìn)程,真的要大大縮短;而戰(zhàn)爭時間縮短了,空間縮小了,唐帝國社會所遭受的戰(zhàn)爭創(chuàng)傷,也勢必會大大減小(京師關(guān)中地區(qū)不會遭受戰(zhàn)火荼毒;國際第一大都市長安,更不會成為廢墟);也更不會死更多的人了。
——所以,此時對唐帝國來說,說最終勝利就在前方不算過分。安祿山面對這個局面,也確實是大為驚恐,連這樣的話都罵出來了:你們這么多年教我反叛,還說萬無一失。今天哥舒翰守潼關(guān),我們幾個月都攻不下來,北方道路又被切斷;敵軍自四方會合而來,我占有的不過汴、鄧幾個州,萬全之機(jī)在哪里!?你們從今往后,不要再來見我!心中煩亂驚懼,可見一斑。
可惜,可嘆,可悲!這個大好形勢的節(jié)骨眼,唐帝國內(nèi)部又出事了!
哥舒翰本來多次拒絕朝廷讓其出關(guān)作戰(zhàn)的命令。這是正確的,因為他知道自己軍隊的質(zhì)量,也知道出潼關(guān)還不到時候;所以他對朝廷的要求與愿望,對楊國忠的不切實際的瞎支招和命令,也一直是挺著不辦。楊國忠也對其猜忌不滿劇增。楊的心腹跟他說過,“哥舒翰如今手握朝廷重兵,若是舉旗向西,危險的是你!”楊國忠聽罷深以為是,于是借口建立后繼部隊,讓玄宗同意招募萬人駐扎在哥舒翰后方,名為防叛軍,實則防備哥舒翰。命親信杜乾運(yùn)統(tǒng)領(lǐng)新軍。哥舒翰知道楊國忠的奸詐陰險,深恐被楊國忠謀算,就上奏請求將此新軍劃歸自己管轄。六月,哥舒翰干脆借到潼關(guān)議事的機(jī)會,借用罪名殺掉杜乾運(yùn)。楊國忠聞之,深為驚怒,所以更屢進(jìn)讒言,說哥舒翰與潼關(guān)守軍的壞話,更有“要警惕哥舒翰這樣的胡人將領(lǐng)成為安祿山第二”這樣的讒言。這干的是跟邊令誠一樣的損事了。哥舒翰部下軍中將領(lǐng),也怨恨楊國忠構(gòu)陷軍隊,飛揚(yáng)跋扈。部將王思禮更是勸哥舒翰,上表玄宗,殺掉楊國忠。不行的話,干脆率一部軍馬將楊國忠劫持出京師,為朝廷除掉這個禍害。哥舒翰起初不答,后來說過:“如此,是我哥舒翰謀反了,而不是安祿山反叛。”——朝中的內(nèi)斗,多么可怕,由此可見一斑。更可怕的,楊國忠安插在軍中的親信將此事密報給楊國忠。楊國忠頭發(fā)根都立起來了!到了這個份上,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啦!
奸佞楊國忠出于一己私利,不顧江山社稷安危,借玄宗之命,強(qiáng)令哥舒翰領(lǐng)兵出潼關(guān),收復(fù)洛陽。皇命難違,軍法無情!這次,哥舒翰實在是拒絕不了了。出兵前,他仍然不想放棄最后的機(jī)會,堅持上奏,說叛軍是故意顯示疲弱引誘我軍出關(guān),安祿山久習(xí)軍事,豈能無備!叛軍遠(yuǎn)道而來,利在速戰(zhàn),我軍據(jù)險,利在堅守。況且叛軍暴虐,無有民心,今內(nèi)部將要發(fā)生變亂,屆時定可不戰(zhàn)而勝之;首要者是能夠成功,何必不切實際的貪圖快!
此時,郭子儀、李光弼也向朝廷上奏,請求引兵北取范陽,直搗叛賊巢穴,將叛賊黨羽的家人俘虜作為人質(zhì),招降叛軍。如此,叛軍必將軍心動搖繼而徹底崩潰。還特意強(qiáng)調(diào),潼關(guān)守軍目前應(yīng)繼續(xù)堅守,拖住南線叛軍并使叛軍疲困,千萬,千萬不要草率出關(guān),而壞整體戰(zhàn)略!——這個戰(zhàn)略計劃,如果付諸實施,可以說能要安祿山的老命!
可是楊國忠又屢進(jìn)讒言,說叛軍疲困無備,哥舒翰有意逗留不進(jìn),戰(zhàn)機(jī)會白白扔掉!唐玄宗深以為是,連派中使嚴(yán)令哥舒翰出關(guān)。郭子儀李光弼哥舒翰的正確建議,李隆基不聽!
哥舒翰眼見正確戰(zhàn)略和意見化為泡影,捶胸大哭!近20萬大軍,最終被逼出關(guān)!
出關(guān)的結(jié)果,哪怕是打成兩敗俱傷的消耗戰(zhàn)也行。可惜不是。是最糟糕最吐血的結(jié)局。靈寶一戰(zhàn),叛將崔乾佑善于用兵,成功伏擊出關(guān)的唐軍。可憐哥舒翰大軍18萬人,幾乎全軍覆沒;逃回潼關(guān)的,僅剩8000余人!8000如驚弓之鳥,缺乏軍事統(tǒng)帥的部隊,哪里能敵得過崔乾佑的精銳叛軍?(哥舒翰被俘了,大批統(tǒng)兵官戰(zhàn)死)潼關(guān)終于可怕的失守!
至此,棋局逆轉(zhuǎn)。安祿山可怕的翻盤了。唐帝國之前的大好形勢,瞬間化為烏有。唐朝廷出的這一手昏招,導(dǎo)致關(guān)中軍隊主力被殲滅,京師兵力已經(jīng)空虛。自此關(guān)中已無軍事力量來抵擋叛軍鋒芒。唐玄宗被迫向四川出逃。關(guān)中地區(qū),天府雄國,繁華長安,開始慘遭戰(zhàn)火荼毒。自此開始,之后的歷代王朝國都,再不是那個恢弘大氣繁花似錦的長安。
之后的平叛歷史就不多敘述了。無情的戰(zhàn)亂,本該早些結(jié)束的;自此更加肆虐唐帝國國土,戰(zhàn)禍波及的地區(qū),也越來越廣。蝴蝶效應(yīng)紛至沓來。戰(zhàn)爭活活拖了八年才結(jié)束。唐帝國在西域的統(tǒng)治和開拓,變成了弱勢直至逐步喪失。地方藩鎮(zhèn)勢力紛紛抬頭。宦官開始進(jìn)入政治舞臺,把持朝政。自安史之亂以后,唐朝內(nèi)部就沒好過。總之安史之亂,將曾經(jīng)強(qiáng)盛的大唐給打廢了。
孫子云,將能而君不御者勝;兵無選鋒而曰北(軍隊無精兵就要打敗仗);存人失地,地可復(fù)得,存地失人,地人皆失;《戰(zhàn)爭論》所述的“戰(zhàn)爭是政治的延續(xù)”等等,這些經(jīng)典格言與軍事思想,在以上說的內(nèi)容中,從正面、反面,無不得到了印證。
總之,唐帝國本來是有條件有能力在平叛戰(zhàn)爭相對短、戰(zhàn)火波及面相對小的局面下,最終打敗安祿山的,以上說的那個態(tài)勢,唐朝如果能腳踏實地的往正道上走,叛軍早就崩潰了,哪用得著打上八年。安祿山叛軍固然強(qiáng)悍,但叛軍屬非正義,沒有民心支撐,而唐帝國畢竟是立國一百多年的帝國,還以尚武崇文著稱,并非沒有出色的軍事統(tǒng)帥和軍隊。像郭子儀李光弼,就經(jīng)常打得叛軍滿地找牙。可惜,有什么樣的政治就有什么樣的戰(zhàn)爭,唐朝白白葬送了短期內(nèi)平叛成功的大好機(jī)會,唐朝與其說是輸在軍事上,不如說是毀在政治上。奸佞橫行,軍中良將遭構(gòu)陷冤殺,關(guān)鍵時刻軍隊遭錯誤指揮;唐朝廷自己,包括李隆基,真是太善于為敵人安祿山幫忙;反過來,安祿山卻根本不給李隆基和唐朝幫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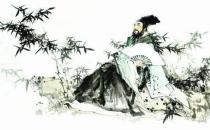

![歷史上的竇嬰是一個怎樣的人 漢武帝為什么要?dú)⒏]嬰](http://www.caoha.cn/uploadfile/2019/1124/thumb_210_130_20191124112618767.jpg)



